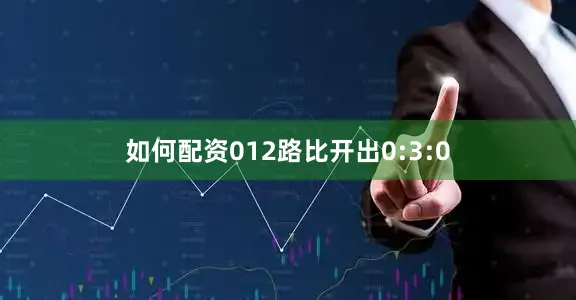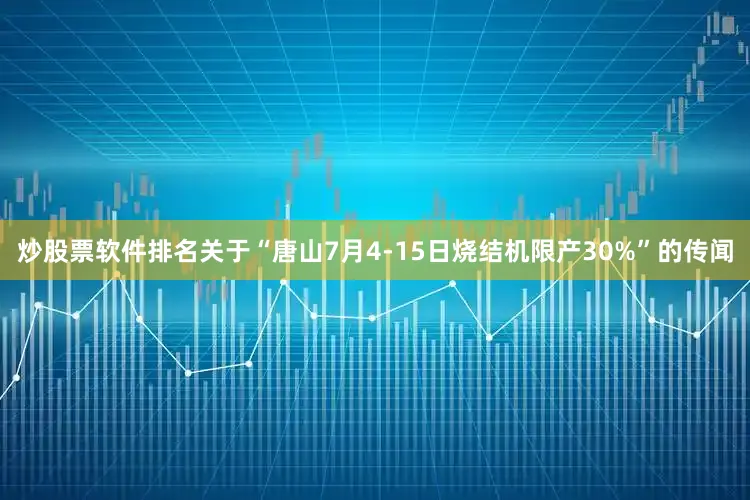《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或许由于国民党在南京时代就相较缺乏独立掌控的资源(经费、交通工具、行政系统上司和隶属关系、和军队实力),所以它中央级党部和党务工作人员在撤退中,相较于军队和政府单位显得更为狼狈和慌乱,遭受破坏程度也更沉重。

许多军队领袖们在从上海战场撤退时,原本期望沿途的国民党地方党部可以发动人民予以协助,却发现完全不见党务人员踪影,为此对党务工作进行猛烈抨击。而原本服务于中央政府各机关的党员们则只是随着所属行政单位撤退,在许久时间内都脱离党的组织生活。至此,国民党在南京十年依靠中央军而生存和发展的缺点暴露无遗。在中央军枪杆子保护下,党工作人员还可以在地方上建立一个有模有样的党组织。一旦脱离枪杆子,党组织就陷入瘫痪。
这个遭遇的后果可以从几个方面看出来。
1、徒有其表的中央党部
首先是党员归队问题。
照常理推之,从武汉撤退后,重庆市成为中央部会极度集中的城市,党员人数也应该最大。但是在1939年初,当时重庆市人口从战前不足20万急速膨胀到约60万人,向党组织归队报到的党员却只有4千余人,而其中70%是中央机关公务员。
如此算来,当时中央机关公务员已经有20余万人,而在中央机关报到的党员人数不足3千人。换言之,在南京时代政府公务员大部分入党,而到了重庆,党政军人员选择完成党员归队手续的竟然降到2-3%。重庆公务员中原本具有党员身份的人数肯定很大,只是选择不再和党发生组织关系,党中央虽然再三努力也无法动员他们归队。
即便是到了1943年中期,根据重庆市党部组织处长报告,重庆市党员报到者仍只有1万多人,而且党籍凌乱无绪,隶属不清。显然地,经过4年抗战,仍然有许多南京时代的资深党员,决定与党脱离关系。这表示在他们心目中,党组织已经无关重要、无价值。
第二个征兆是,即使在选择归队的党员群中,党组织和活动仍然松散无章,而这个趋势正是由党的中央组织领头示范。
中央党部迁到重庆后(1938),职员人数膨胀到超过1千人,但是却无事可做,也缺乏工作能力,造成中央党部变成一个极度臃肿的官僚机构,内部人事处理成为极大困扰,丝毫看不出它能够作为全党表率去营造战时士气高涨的气象。
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在任时以敷衍了事著称,甚至被赋予一个绰号称为“叶婆婆”,讥笑他只光做好人而不做事。而副秘书长甘乃光则抱怨他无权过问许多党部事务,因为整个机构被三数人把持一切。党部办事无能、人事纠缠、制度欠缺、过去松散,现在依然如此。国民党的首脑部门如此不健全,党务难以推展成为理所当然。
根据陈克文记载,早在1938年初就可以看到党务工作颓废迹象。比如说,抗战不久国民政府为了促进抗战建国目的,在珞珈山举办了高级干部训练班。中央党部作为重点单位,率先指派了职员600人去受训。但是在开学数日之间(6月1-9日),这些党干部因为生活辛苦而逃学者竟达半数。

而且他们也显出知识水平低下得惊人,连简单数学习题(圆周率)都不能解答,招致蒋介石痛斥他们是现代版的“八旗子弟”。党政干部训练在抗战时期是一件大事,创办中央训练团的目的,是把全国中上级党政干部全部予以训练,以促进抗战建国功能。到了1944年,形式上经过党政训练班训练的人员已经达到2万2千人,但是政府费时费钱却缺乏效果,令蒋介石高度失望。
到了1939年党中央单位干部们的弱点就更形彰显,首先是上级领袖们率先轻视和规避党务工作,下级党员们当然有样学样而变本加厉。
当时一个具体案例是,蒋介石手谕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制定一个公务员生活辅导办法,其中规定中央各机关的党干部应该主导该机关公务员每周举行一次小组会议,并且进一步规定小组会议工作内容共有6项,前3项是检讨和改进过去一周中工作,后3项是阅读和研究具体问题并提出报告。
这个主意虽然很好,但是在行政院内部就无法推行,因为院内许多党小组组长都阳奉阴违拒绝开会,而其他各部会机关亦复如此。然而他们呈送给蒋介石批阅的报告则冠冕堂皇,夸称开会认真,成绩斐然。事实上即使极少数小组果然如期开会,与会者也无话可说,只好草草收场。
由于历来会议都是由上级训话下级听训,很少上下级党员可以自由沟通者,所以如果上级党员不关心党务,则党务工作必然流于形式主义。
难怪陈克文感叹,“党部现在最大的毛病确在于工作的纸片化和机械化。下级对上级固不免敷衍苟且,上级对下级也一样的搪塞因循,毫无清新活泼的气象。”他指出,党部的“官署化”是党务办不好的重大原因。

同样情形表现在“新生活运动”政策的推行。查该运动首创于南京时代,深受蒋介石夫妇关切,战时依然如此。但是运动虚多于实,王世杰就坦白指出,运动的领导人物在内心也对于运动缺乏诚意。总干事只能做表面工作,不能鼓励知识分子参与。沦为宫廷式做法,只是讨好蒋氏夫妇而不能唤起广大人民响应。党在此项群众运动中几乎没有发生作用。
2、党组织的运作
上行则下效,行政院党务已然如此松散,其他中央部会的表现就更是等而下之。因此当行政院内举行国民党党部会议时,大众党员对党的态度同样冷淡,不热心参加党的会议。党的工作没有人肯做。而院内党部办事也公文化,会议没有内容,虚耗时间,令人生厌。党务小组会议时,经常是大家面面相觑不发一言的尴尬场面。在各机关,党员不重视参加组织活动,把区分部和小组会议看成是无聊而尽量逃避。
1939年夏季,行政院归队的党员仍然不到全体职员的半数,众多旧党员虽经多方催促也执意不肯报到归队,即使报到者也不肯接受党务工作。引起陈克文感叹,行政院“区党部成立已经半年,快要改选了。半年来的成绩,回顾起来,可以说是等于零,新党员也只增加了一个。”所以院内党部形同虚设,完全不能发挥政治战斗力。这种现象也遍及整个重庆市。
1939年4月份,重庆市市党部郑重宣布召开会议,行政院事先已经预测重庆市只不过是虚张声势,想要向上级邀功,其内容必将空洞而毫无意义,因此只派了2人去参加,应付场面而已。以行政院是全国政务的最高领导机构,重庆市是抗战大后方的首善之都,它们的党务领导人对党务的认知如此轻佻,心态如此玩忽,则其他地区的沉沦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此时期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状况是,大片土地已经落入敌手,或者处于敌我双不管地带。它包括河北、察哈尔、江苏、山东等省份或是所谓的游击区。它们的党务工作本应该由中央党部和政治部统筹负责,但是由于两者无法展开工作,蒋介石只好特别设立一个新组织——党政委员会——希望能够开拓党务。但是该会在成立之后,党政领袖们却躲在重庆市的安全环境里争夺权位和划分地盘,完全忽视游击区的现实需要。
到了1940年初,情形更为恶化。行政院党小组委员会已经好几个月都不曾开会,许多小组组长举出各种荒唐理由作为搪塞,就是不肯召开会议。照理说,行政院区分部共有80余位党员,仍然可以形成力量做出成绩。
但是当各小组长本身就不热心党务,则党员也对党务冷漠待之。党中央领导尽管口头叫嚷要注意基层组织,但都沦为空谈。稍有地位的党员对于党内基层组织会议和工作都不肯参加。无形中酿成一种轻视基层组织的心理,基层组织当然由此无法巩固。

一个充满讽刺而又反映真实情况的例子是,1940年3月,重庆市党部锣鼓喧天地召开全市所有区分部的“书记会议”,并且由中央党部秘书长亲临主持。然而到会150位出席者却鲜少“书记”身份,而是由各机关指派低层人员滥竽充数。
正因为中高级官员不屑费心党务,所以这种以低阶党员替代各机关党务领导人,参加各种活动成为当时普遍现象。在这种气氛下,党务工作做不出成绩,毫不奇怪。
到了1943年中央监察委员会接到许多攻击重庆市党部的报告,因此决定派员前往视察,而且还先行通知,以便后者有充裕时间做好准备。岂知届时发现市党部对于工作只取敷衍态度,主任委员杨功达一味抱怨经费不足、中央不信任、不能办事等一片牢骚。他同时指出党部委员们又在外兼差和忙于交际、写文章、办报纸,无暇顾及党务工作,更完全忽略党的基层工作。
这番接触逼得监察委员会不得不向组织部提出警告,以该市为陪都所在地,党务工作如此松懈玩忽,实感痛心无比。当然整个事件无疾而终。
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个生动的案例:行政院党部号召党小组开会讨论“如何推行地方自治”。照理说,行政院主管地方自治工作,本就应该最关心这个议题,而党部尤其应该是推行地方自治的生力军。但是参加者事先既没有进行研究也不感兴趣,以致讨论时空气沉闷缺乏内容,纯粹走过场,甚至有人公然在会场睡觉。行政院其他各小组也是一样。
说到底,中央阶层党务最大的问题是许多机关内,有地位和权力的党员打从心底轻视区分部,不屑加入区分部工作,甚至不向区分部报到,目的就在避免参加区分部会议和承担党务工作。在这种情形下,一般党员也不重视区分部,不利用区分部去训练党员,更无法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和工作。说得更直白些,中央党部的官员有将无兵,只顾自己争权夺位,而低阶层党员在各机关内部缺乏威望和吃不开,就只好借党的派系关系做自己的政治进身阶。

中央党部组织部长朱家骅,曾经写过一本册子叫“党的组织问题”,对于组织原则和国民党组织上的缺点,都表达过见解和针对方法,但是无法实践自己的理念。事实上,国民党内主要领袖们并非不懂理论,而是不能付诸实行,导致理论和实践彻底分家。这种情形糟糕到让陈克文在1945年彻底灰心,甚至建议干脆取消区分部。
真是对中央党务最严峻的宣判。
3、派系角逐的战场
正是因为党中央组织散漫和缺乏活力,而无法向外展示战斗力,因此只能集中精力把党部内部职位当成为派系分赃的目标物予以争夺。
首先是尽量扩大自己单位的编制,招聘更多人员,一方面成为政治酬庸筹码,同时也借以壮大声势。造成党务组织益形成为一个头重脚轻局面。
其次是由于党各级委员是被上级委派,而非由选举产生,更造成下级党部空虚。因为与其在基层党部埋头苦干,不如巴结上级要人以取得信任和提拔。于是下级党员竞而奔走争宠,置基层工作于不顾。
但是由于党中央控制范围终究有限,所以除了中央党政机关之外,各省党部委员名额也成为中央派系角逐的猎物,其动机只是求扩张派系势力,而不是关心该省的党务推行。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山东省党部。山东省辖地遭受分割为游击区和敌后区,各地在名义上仍有党部存在。但是当何思源被陈立夫委派为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时,他不但无视于在山东省当地党员们的提名和选举权,想一手包揽省党部委员的任命权,甚至意图任命滞留在重庆或是非山东籍人员冒名成为山东省党部委员,引起其他山东籍在重庆的党政官员的愤怒。可见有些省份的省党部完全是架空机构,和本省基层根本脱节。
中央党除了组织部之外,还有一个监察体系,其最高单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而各个等级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是督促和改进该等级的党务工作。

但是中央监察委员会本身人员短缺,经费拮据,下级监察单位更是瘫痪无力,或是报告内容空虚不实。更重要的是,它的职权完全不受尊重,许多党政军单位对于监委会在法权之内作出的决定不予执行。王子壮担任中央监委会秘书长多年,是它实际工作的最高负责人。
但是他在1945年初回顾战时党务工作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央监察工作人员本身就不健全。在大环境下无法避免污染,为了生存而宁可依附派系而失去公正。中央级监察工作不端正,下级监察工作更是有名无实。
他特别举出重庆市监委会为例,该市监委会委员都是兼职,因此无暇顾及监察工作,中央监委会数度派员督促也毫无效果。王子壮感叹道,重庆是战时陪都,原本希望它可以做出示范。但是如此空虚,则其他省县的虚假就更不难想象。
4、领导人的无能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党务领导人的政治视野和使命感问题。陈立夫作为党组织部长期负责人,他的心态或许可以提供一个有价值的信息。
1945年春天,陈立夫重掌组织部又积极主持六全大会筹备工作,对于党的过去成绩和未来发展具有极大影响力。
他在一次组织部会议上,对党过去所面临的危机做出的一个全面性回顾时,开宗明义地指出,党在战时应该有四方面任务,即“管、教、养、卫”。
这个说法立即显示陈立夫的思路和南京时期一成不变,完全没有考虑到抗战时期党的挑战及使命,和南京承平年岁应该天差地别。
更重要的是他继之抱怨党功能已经被其他单位彻底僭越取代。
他提出的具体说词是:
(1) “管”的工作被省政府取代,尤其是当省主席兼任该省省党部主任委员时,中央党就“不敢开口”,只能眼见政治腐败而无能为力。(2)“教”的对象是青年党员和干部,但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夺取了青年政治活动领导权,党组织完全无法发挥作用。(3)“养”的对象是社会事业和发展社会团体,但是自从政府成立社会部以后,也剥夺了党的活动空间。(4)“卫”的目的是追求国民党的自保和与异党进行斗争。但是此项工作已被特务机构专擅,一般党员认为事不关己。
换言之,战时党务工作不能展开,不是党领导人的错,全是别人的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十年是一个政治经济生活相对富裕安康的环境,党即使在中央军枪杆子保护之下,也只能在狭小地区内推动“管、教、养、卫”工作。

但是在抗战八年中,外有强敌压境,内有地方实力派相煎熬,大后方社会形态和民生环境与南京时代截然不同,而陈立夫等党领袖们依然墨守成规,思维不能跳出南京时代框架。
在这个面临重大危机时刻,国民党领袖们却只能怪怨他人挡路挤压或僭越,而完全看不出党可以在自己领导下去启动革命斗志,和开辟一条革命新路。他们对于培养干部、监督军政、组织民众、巩固基层、发挥“传送带”功能等等各方面,几乎毫无想法,也可以让我们对于战时国民党领导层的短视和颓废心态得到更多了解。
如此的党中央机器在八年中完全陷于孤立,结果并不令人惊讶。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众盈易配,个人配资是否属于非法经营,配资门户论坛官方网站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